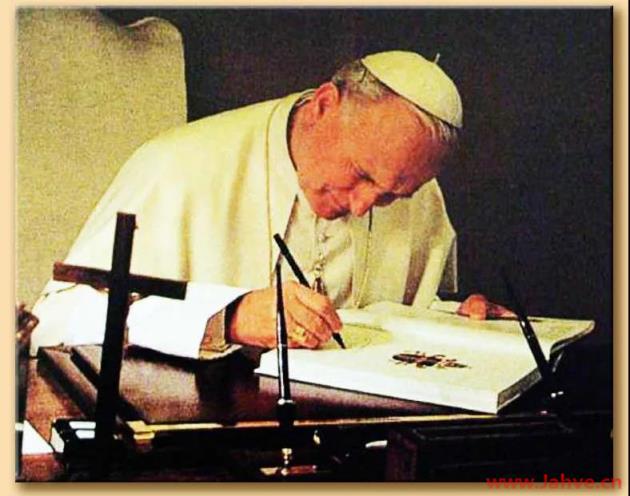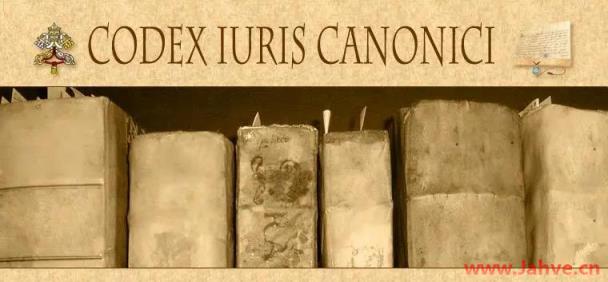前言
假设我们做一个问卷调查,请天主教的信友们遴选出最重要的教会书籍,毫无疑问,位居首位的必定是那本全球流行最广的典籍——《圣经》,即在天主圣神默感下写出,以文字形式保存的天主圣言。倘若我们继续询问,仅次于《圣经》的是哪一本读物,大家也许会写出《天主教教理》,因为它囊括了天主教教义主要和基本的内容。如果继续下去,之后被列出的或许是《圣人传记》类的作品,所谓行为人师,学为世范,圣人历来是教友师法的楷模与信仰的杰出见证。而本文的探究对象却是一本十分重要、但却又常被忽略的教会文献,即《天主教法典》。在此所回应的问题是:法典之于教会的重要意义,亦或为何教会需要法典?内容涉及教会现行法典(1983年版)的产生背景,它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关系,及其对教会的意义。本文目标在于提高教友对法典的认识,并由此激发学习法典的渴望。虽然教会当局直至二十世纪初才对教会的法律条文进行了系统编纂,并正式推行了第一套官方法典(1917年),但对于教会团体而言,法条规诫并不陌生。《圣经》中就涉及很多与法律相关的经文。例如,旧约前五部书,也被称为法律书,“因为在这五卷书内,包含着旧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梅瑟给以色列人所宣布的法律,为此圣经上多次称五书为‘法律’。希伯来人称之为‘托辣’”[1]。又如新约中,耶稣基督强调祂来的目的并非在于废除旧约的法律,而是以新而卓越的形式将其纳入新约的满全之中[2]。旧约和新约本身当为最高的法律,是“基督宗教法律”之概念的第一层含义。自教会建立之初至1917年,教会的法律条文即以历代教宗所颁布的法令及大公会议文献的形式存在,是“基督教法律”之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如果按这一层含义来检索基督教法律的文本,一定卷帙浩繁。教会自古以来即保有改革和更新其法律条文的传统,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变法而变法,而是对其神圣的建立者基督保持忠信,以便更好地适应所处的时代,并以更好的方式履行主基督赋予她的使命[3]。1959年1月25日,刚继任伯多禄传承人三个月的教宗圣若望二十三世,在城外圣保禄大殿庆祝外邦宗徒瞻礼时,隆重颁发了三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宗座谕令: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修订1917年版的《教会法典》,以及召开罗马教区会议。之后,教宗圣保禄六世在修订教会法典的开幕式(1965年11月20日)讲话中,也明确重申了修订法典的急迫性。他提出,教会法是溯源于教会的本质,它的根源在基督托付于教会的治理权,以及为达到永恒救恩的牧灵照顾之目标上;同时也指出此次修订不仅是法律的重新整理,且更是要适应新的思想和新的需要[4]。对教会法修订的工作历时近十八年之久(1965-1983)——经过漫长的研究、修订、审议工作之后,新法典终于1983年1月25日正式颁布,并于当年将临期第一天生效 (1983年11月27日)。
[1]《圣经》思高版,“梅瑟五书引论”。
[2]参见: 教宗圣若望ˑ保禄二世,《神圣纪律法典》宗座宪章,(梵蒂冈:1983)。
[3]同上。
[4]《天主教法典》中文版 (河北信德社 2003)引言18页。
2、1983年版教会法典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关系
毋庸置疑,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为教会在近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此次大公会议的文献亦对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的各项牧灵和管理工作有着指导性的作用。遗憾之处在于,教会法典与此次大公会议之间密切的联系似乎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如果阅读法典条文的脚注,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众多法律条文参考、甚至直接援引了梵二文献。宗座法律条文修订委员会成立于1963年3月28日,当时大公会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委员会一致认为修订工作必须等到大公会议结束才能开始,因为法典的修订必须建基于大公会议的精神之上,由此才能保证法典修订的法则和方针与大公会议保持同步,即“更新基督徒的生命”[5]。在众多对教律、神学、牧灵、及民法有专长的主教、司铎、会士、及教友的反复斟酌推敲下,新法典于1983年1月25日问世。据统计,当时参与修订的委员包括了来自五大洲三十一个国家的105位枢机、77位主教、73位教区司铎、47位修会司铎、3位修女,及12位教友[6]。正如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所言,“这部法典,就其内容而言,实乃全体主教兄弟们对教会的集体关怀。与大公会议类似,此法典应被视为集体合作的结晶,是集合了普世教会的专家与学术机构之大成”[7]。教会的众多学者也断言,《天主教法典》应被视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最后一份文献[8]。因此,《天主教法典》理应享有与大公会议文献同等的重要性和关注度。
[6]《天主教法典》中文版 (河北信德社 2003)引言20页。[7]参见: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神圣纪律法典》宗座宪章,(梵蒂冈:1983)。[8]Msgr.Laurence J. Spiteri, JCD, PHD, Canon Law Explained: A Handbook for Layman,(New Hampshire: Sophia Institute Press, 2013), p. 20.有人说,“教会是一个爱德的团体,倘若以爱德行事,何需法典?” 毫无疑问,教会是一个基于信德、望德、爱德,以及在恩宠中成长的团体,但法典的产生及更新不但丝毫不会改变这一事实,反而其目的恰恰是要在“教会团体中建立正确的秩序,使得信仰、恩宠、及神恩既在教会团体中,同时也在个人的生活中都享有首要地位”[9]。也有人声称,“我不需要法律,也不需要教会,我直接和天主相连。” 这实则是异端邪说,这样的“天主”是某些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创造出来的,而真正的天主藉着自己的圣子耶稣基督创立了教会,并愿人藉着教会团体而获得救恩。法典与“教会论”紧密相联,除非明白“何谓天主教会”,否则无法理解法典存在的必要性。教会是天主子民按照以服务为宗旨的圣统制等级所组成的一个有形可见的社团组织[10]。教会的本质也被定义为“天主的子民(Populus Dei)”、“基督的奥体(Corpus Christi)”、“共融(Communio)”、和“圣事(Sacramentum)”[11]。然而在一个有形可见的、由人组成的教会团体之中,要满全上述关于教会所描述的各个属性,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不可或缺。也只有藉着法典,个别教会和普世教会之间、主教个体或主教团集体领导与教宗首席之间、平信徒与神职人员之间、以及天主子民的个体性与教会的团体性之间的“天赋圣统组织架构才能得以显示,从而藉着教会神权和圣事的施行而履行主基督所赋予教会的使命”[12]。对于有形可见的教会而言,为维护圣统秩序、保证教义的正确性、保障基督信徒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圣秩人员的权限等,建立法律是必要的。因此教会法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耶稣治愈癞病人的故事中(玛8:1-4),治愈病患之后,耶稣叫他去“让司祭检验,并献上梅瑟所规定的礼物,当做证据”。耶稣作为天主子,职位和能力完全超越于梅瑟,但祂仍然谦卑地服从于法律。癞病人在天主子治愈之后也比一般人更健康更洁净,因为其治愈有着圣事的维度;但基督却让他谨守法律,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多余的程序,实则意义深远。因为唯有藉着法律,那被洁净的人才能再次被接纳到团体之中,而只有在团体之中,他的个体性才能得以彰显。同样,教会的法律并非一系列限制个体自由的条条框框,而实是保护我们天主子女尊贵身份的一大恩宠;同时,作为基督奥体之肢体的这一属灵身份,也只有藉着教会团体才能变得有形可见。
[9]参见: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神圣纪律法典》宗座宪章。[11]参见:《教会宪章》第1, 4, 8, 9,13-15,18,21, 24-25, 48 号。《天主启示宪章》第10号。《牧职宪章》第32号。《大公主义法令》第2-4,14-15, 17-19, 22号。[12]参见: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神圣纪律法典》宗座宪章。 ·························································总而言之,如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所说,“教会法典作为立法的主要文献,以天主的启示和教会圣传中的法制和立法传统为依据,以维持个人和社会生活,以及教会本身活动的必要秩序,乃是不可或缺的工具”[13]。并且,法律与神学紧密相连,法律不单单是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而是教会为了天主子民之益处,将其对天主的启示和对神学的理解以法律的语言呈现出来,让人回归于法律之下、教会之内。正如法典1752条所强调:“应切记,人灵之得救,在教会中常应视为最高无上之法律”。在此呼吁教会的牧者和天主的众子民,能加强对法典知识的了解,增加对教会法典的热爱,以便善用法典重建中国教会的秩序。
[13]同上。